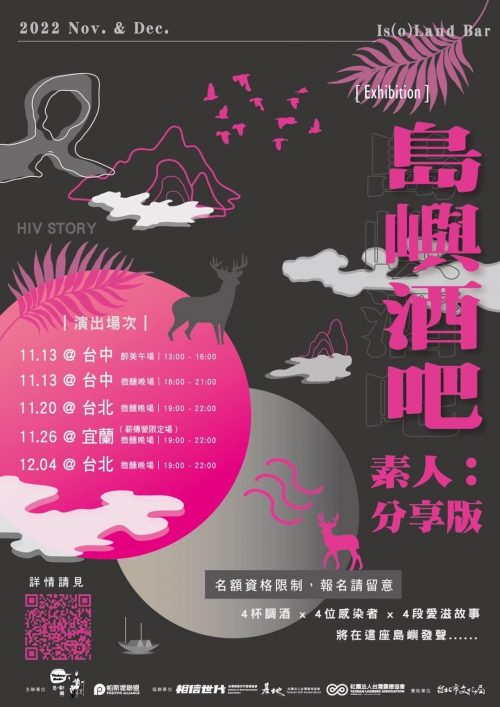分享人/H的生命自述
目前四十多歲的H,是一位國小老師。在他成長的年代,社會討論LGBTQ族群的聲音並不多,因此直到三十歲以前,自己是男同志的秘密一直藏在他的心中。他甚至心想,是不是就假裝以異性戀的身份度過一輩子?但是在三十歲以後,他發現自己再也無法獨自承受這個秘密,身心都開始出狀況。他開始試著向朋友、同事表明身份,也鼓起勇氣跟家人出櫃。過程中,他發現每個人對同志族群的刻板印象,都在自己出櫃以後開始有了轉變。如今社會風氣漸開,他的故事也成為了最好的提醒,讓更多人知道一位男同志的生活,其實和大家並沒有不一樣。
「爸媽也有一個櫃子,叫做我的兒子是男同志。」
時間又過了兩年,有一天我回家時,媽媽說姑姑下午有來家裡,我爸就把我的事情跟大家講。我說沒關係,兒子不結婚其實爸媽的壓力很大,我也都可以理解。雖然在我的面前不提,但是他們的兄弟姐妹也都還是會問,所以我爸就自己跟他們說開了。當天我也沒有太多情緒,直到後來問我爸為什麼那天突然想講?爸爸就說:「親戚大家都知道也沒關係,不然一直問也很煩。」我就跟爸爸說,雖然我是當事人,但是要親戚說出這些事其實很不容易。
從那時候起,爸爸的親戚就知道我的情況,不太會再提到結婚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整個家族還是有一種不能說的秘密的氛圍,雖然大家會避談結婚的事情,卻也不像異性戀的家庭聚會一樣可以拿出來輕鬆討論。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推動同婚法案的那一年。當時為了連署法案要簽同意書,我就在家族聚會前跟爸媽說我要帶去給大家簽署。我帶了一個資料夾,裡頭是一整疊的連署書,但是聚餐時又一直不敢提這件事情,一直到結束前,我媽突然說:「你不是有東西要給大家簽嗎?」我才把連署書拿出來給親戚們簽名。我記得當時還有從加拿大回來的堂姐,她帶著姐夫和孩子一起來聚餐,因為加拿大已經通過同婚很多年了,所以她很自然地用英文跟孩子解釋舅舅現在在做什麼,台灣要推動的是什麼法案。當大家簽完連署書拿給我的時候,我一邊收一邊掉眼淚,我想那應該是很害怕,卻又覺得被支持、很感動的眼淚。
我覺得相較於爸爸,媽媽反而是比較保守的。在爸爸的親戚知道以後,我就有暗示性地跟媽媽說:「阿姨、舅舅他們知道也沒關係唷。」我媽說她有特別提醒大家不要問結婚的事情,但是沒有講我是同性戀。一直到有一年,我哥準備要結婚了,喜帖都已經寄給各個親戚朋友,媽媽打電話去邀請大家來吃喜酒,電話裡就又被問到什麼時候輪到我結婚。我媽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就支支吾吾的,等到她掛完電話,才跟我爸抱怨大家又在問我結婚的事情,我爸就跟她說:「現在就打電話回去,每一個跟他們說H是同性戀。」然後,我媽也就真的一個一個打電話,幫我向大家出櫃。這是回家以後媽媽才跟我說的,我雖然嘴上跟她說都沒關係,但是一回到房裡我就大哭,我完全可以想像媽媽被大家逼問我結婚的事,還要一個一個打電話跟親戚講我的狀況,那個不知道該怎麼面對的壓力,就覺得在櫃子裡的父母,其實壓力也很大。
我想他們其實也有一個櫃子,叫做「我兒子是男同志」。其實父母擁有更少的資源來面對這些議題,他們的同儕或是成長背景,以及接收議題的管道都不如我們,讓他們在很多時候都需要自己消化情緒。所以很多人說,當我們在出櫃的時候,父母同時也進入櫃子;他們很多時候會需要更多陪伴,我覺得這些都是親子之間共同要去面對的課題。
我是在跟爸媽出櫃以後才到基地擔任志工。我會跟他們說我到什麼單位服務,認識什麼樣的人;也會刻意把志工朋友帶回家讓父母認識,無論男女、男同志、女同志,跟他們說這是我的朋友,讓他們碰碰面,希望他們有具體的印象。我媽有一次就跟我聊說,你帶回來的那些男生都不像(同志),我就問她說要怎麼樣才像?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在他們的成長環境中,不知不覺累積許多的社會框架和刻板印象,而我試著建立一個管道和他們溝通,讓他們更加了解我的世界,而不是憑空想像。
最早我開始參加同志遊行時,媽媽會很怕我被媒體拍到,我自己也會很擔心;但是現在,她已經會主動跟我說在電視上看到同志遊行的事情了。我覺得我們都在改變,就像面對自身的議題需要時間一樣,我想父母也需要時間去消化和面對。
「我們的每一次出櫃,都在給對方一個認識同志的機會。」
在我服務的國小,有一群比較要好的同事知道我是同志。我有一群很要好、年紀差不多、一起進學校的同事,大概五、六個人,只有我是男生,其他都是女生。我常常科任課沒事就會找她們聊天,結果每一位都跟我傳過緋聞。學校經常就是緋聞滿天飛,我知道這些事情以後,有段時間反而不太敢和她們太靠近,怕會影響到她們。但其實我還是需要自己的社交圈,不可能都跟同事不互相往來,只是很多的事情都不能講實話。
有一年我開始刻意規劃,希望到了某個年紀可以活得自在一點,不要太考慮別人,所以我計畫在三個朋友群出櫃,同事的朋友群就是其中一個。我在假期約了一個飯局,過程大概先鋪陳一下開場白,告訴他們我們認識了很多年,希望他們可以更認識我,然後就開門見山的說,我是男同志,然後接下來他們就會有個提問SOP:你什麼時候知道、家人的反應怎麼樣、你的反應怎麼樣、現在是不是單身、角色是男生還是女生……被問的都是這些考古題,解釋多了就會很上手。每一次講到跟爸媽出櫃的橋段,大家都會對於我爸媽當場的反應很吃驚,有些朋友甚至感動到哭了,我就想說我都沒哭她在哭什麼(笑)。但就像朋友說的,其實我們的每一次出櫃,都在給對方一個認識同志的機會。
我是某些同事人生中第一位活生生的同志朋友,因為國小老師的生活真的很單純,大學也是同一群人,到了職場還是同樣類型的人。在向他們出櫃之前,我就曾經在臉書寫下:「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因為我怕你認識了真正的我。但是,那卻是唯一的我。」但我覺得讓朋友認識真正的我這件事很重要,因為台灣的性別教育很奇特,讓一群沒有接受過性別教育的人,在第一線教導學生性別教育。在我們那個年代,小時候是沒有性別教育的,只有簡單的性教育;但是現在卻要這一群人在國小、國中、高中教學生性別教育。其實老師們對於性別教育也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覺得自己的每一次出櫃,都是很珍貴的經驗,讓大家能夠更了解同志的生活日常。
「說到出櫃最大的改變,就是我不用再說謊了。」
至於談到對學生出櫃,我覺得國小學生對這個議題還不是太敏銳,所以我對班上的學生並沒有談過這個話題。但如果課堂講到一些關於家庭、性別的事,我會稍微提一下台灣的現況,不太針對支持或反對同性戀的狀況來說明,而是告訴他們台灣現行的法律,男生可以跟男生結婚、女生可以跟女生結婚。很明顯會看到有一些孩子是會皺眉頭的,因為家庭教育和家長的觀念還是會有影響,我也會藉機問學生:「你覺得為什麼不行?」會跟他們有一些討論,但不會給出正式、固定的說法。我覺得學生都還在大量接收資訊的階段,他們還在找尋自己的想法,只能透過引導讓大家一起來思考。
選擇不對學校的學生出櫃,除了我不清楚同事、長官或是家長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以外,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顧慮。我同時是一個老師,又是一個男同志,跟孩子們相處的時間那麼長,會擔心讓學生知道以後,他們對男同志的印象就只有這一個。畢竟我是他們生命中第一個男同志樣本,所以我必須維持好自己的形象,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有壓力的。雖然我認為沒有什麼完美的男同志,但是因為我還沒有辦法確定自己給學生的東西都是對的,所以心中會有一些壓力,但我認為這是我個人的議題。
我們的同志身份確實可以讓我們經驗到很多一般人沒有辦法接觸到的事情。我們能夠感同身受弱勢的經驗,從小就比較能夠同理和體諒不同的處境。當然異性戀的生活也有很多包袱,來自生兒育女、親朋好友、社會框架等,但是我覺得同志的伴侶生活也有許多議題要面對。所以,我現在還沒有辦法很自在的告訴大家,我覺得當一個男同志很不錯,我覺得台灣社會也沒有讓我有這種安心的感覺。
當然社會也有在改變,無論是在職場上,或是各個年齡層對LGBTQ話題的接受度,都跟以前不一樣了。如果要說到出櫃以後最大的改變,就是我不用再說謊了。過去和家人、同事相處,會有很多部分需要用謊言來包裝—今天要跟誰出門、發生什麼事情、如何面對同事介紹的對象,生活中常常要編織故事、戴上虛假的面具,講一些根本不是事實的話。所以出櫃對我的影響就是,很多事情可以開始說實話了,至少可以讓我用比較靠近自己真實的那一面,跟身邊的人相處。這讓我的身心比較放鬆,也終於不用一直戴著面具生活了。